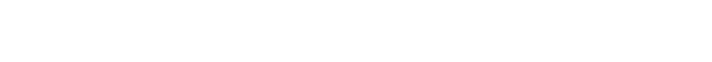編者按
作為國內首個將國別區域研究作為學校發展戰略的高校,上外鼓勵師生放眼世界,在多元文化環境中砥礪成長,廣泛而深入地開展海外田野調查。
近期,上外聯合《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報道了上外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研究員汪段泳在阿富汗做田野考察的經歷,在他看來,隨著田野調查步步推進,當越來越多的“違和”被發現,離真相或許也就越來越近。今天,我們通過原創視頻和文字,講述更多關于他的故事……
“一頭撞到了非洲去”

2018年,在吉布提進行田野調查時坐在皮卡車后斗上向鹽湖進發
(趙裴 攝)
“其實當時我都不知道自己的這第一次非洲之旅在學術活動上算什么性質,直到回來后在本校第一場‘漢堡視界’座談會上和師生們分享見聞,當場被一位真正的田野專家詰問,就是以做苗寨民族志聞名的余華教授,后來又被之‘誘導’,這才知道原來我這就算是‘田野調查’了。其實對我來說,這趟初行非洲基本是個偶然事件,很有個‘腳踩西瓜皮’的感覺。當時也沒想到,后來會在這條‘不歸路’上越滑越遠。”汪老師笑著說道。
從那時開始到現在,已過去了十一年有奇。其間,汪段泳先后走過了埃及、安哥拉、尼日利亞、津巴布韋等十數個非洲國家,加起來在這塊外界對之充滿奇幻想象的大陸上生活了將近四年。兩年多前疫情正熾時,又輾轉赴巴基斯坦開啟新的田野調查項目。最近一年多來,他又將目光投向了局勢劇變后的阿富汗。

田野調查無坦途
采訪中,汪段泳一直在為田野調查“去浪漫化”:“我有時會和同行交流,你有沒有被當地人敲詐、欺負、虐待過?有沒有被歹徒拿刀劫持過?有沒有在貧民窟路邊攤買過吃的?有沒有在荒郊野外喝過土坑里的臟水?如果都沒有,就我個人經歷而言,我們對田野調查的認識或許不太一樣。”當然,汪段泳再三強調,以上四問僅僅是基于其個人在非洲、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狹隘經驗,并不具有科學性,更不具普遍意義。
在阿富汗山區顛簸趕路,車輛出故障成常態。最險的一次是野車剎車完全失靈。周邊荒山野嶺人煙稀少,最近的修車點也在百公里外。“求援脫困的時間遠超預期。盡管車上有飲用水和食品,但還是不夠。”他說,這時就不能太講究,只要沒有肉眼可見的污濁,泥塘里的水也要喝下去,“最重要的是保持體力能干活。如果還要保持國內衛生習慣,就田野工作而言是不適合的。”

“住在酒店里的大部分是華人和中國人,襲擊就從我頭頂上的隔壁房間開始。”密集的槍聲持續了約三、四十分鐘,中間夾雜著大小不一的爆炸聲,疑似來自手雷和炸彈。后來還出現了更大的爆炸,把整層樓的窗戶都震飛了。從槍響到被解救,他度過了約兩小時。

12月13日,作為喀布爾酒店爆炸親歷者接受東方衛視連線采訪
盡管在多年來的海外田野調查過程中,親身經歷險境的情況不在少數,但汪段泳依然認為,即便越來越多人給田野調查戴上耀眼光環,保證人身安全應是任何工作的前提,田野調查不應以進入風險地區為選擇調研地域的標準,更絕不應以獲取風險信息、感知風險過程為研究目標。這位經濟學博士看來,每個人的行為都要有明確邊界,不要產生“負外部性”。

發現之旅
這些年,汪段泳的田野調查既是驚險之旅,也是發現之旅。
剛到喀布爾幾天,他就被路口檢查的塔利班警察扣留并帶到小黑屋。之后他通過交流發現,這位警察是當地一所名校的農學畢業生,還參加過國際學術會議。這與外界對塔利班的固有印象不同,汪段泳于是壯起膽子和對方聊了起來。

2022年9月,在喀布爾郊外拾荒村進行田野調查
名校學生為何會當塔利班警察,背后有沒有這個國家深層次的原因?每段類似的小插曲,往往能為了解這個神秘國家打開一扇窗戶。于是,隨著田野調查步步推進,當越來越多的“違和”被發現,離真相或許也就越來越近。

2022年9月,在喀布爾召開的中-阿-巴經濟合作研討會上
作為唯一中國學者作學術報告
1:20
“田野調查不應該被過度迷信甚至被神化。”汪段泳認為,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田野調查并不比其它的研究方法更便捷、更高效,它的效用同樣是建立在任何學術活動都應有的艱苦勞動的基礎上。當大家都欣賞“田野”這個炫酷光環的時候,需知它只是“調查”的一種實現方式;而學術研究中調查工作的絕大部分,也是更為基礎、更為重要的,是艱苦程度要高得多的案頭工作。

由此可見,田野調查從來不是“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相反,很多時候由于闖入陌生領域,探索過程就是“以無知求未知”,甚至是“摸不著頭腦的摸索”。這一過程中,要想保持充分的常識感來應對不確定性,那準確掌握方法論尤為重要。這也就再次說明,探索和調查并非只發生在田野現場,而是需要平時不斷案頭積累,以提高自身素養。
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目前被戴上了無數耀眼光環的田野調查,其實只是整個學術研究鏈條上的冰山小小一角,不能忘了它能浮出水面,基礎是要付出更大量、更復雜、更艱苦、更漫長的學術準備。。

從這個角度來說,真正的田野調查從不是讓研究走上快速路的終南捷徑,相反它需要準備更多知識、投入更大工作量、延展更長成果生產周期。現實情況是,一邊是田野調查“變現”過程相當漫長;另一邊是在知識半衰期迅速縮短的當下,學術體制要求學人快速成長,田野調查的性價比需精細計算。
而對于汪段泳來說,能得以長期在海外持續進行田野調查工作,是因為一直得到方方面面的鼎力相助。其中,他特別感念學校和學院始終如一給予他的實際支持。“以實際的制度創新以支持區域國別研究,給我在海外留下來做田野調查的空間,這種管理上的靈活性對我來說是一個最為巨大的幫助。”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國內首個將國別區域研究作為學校發展戰略的高校,上外近年來逐步建立研學一體的“專業化”“特色化”田野育人機制,越來越多的師生希望投身海外田野調查,這讓汪段泳倍感期待:“整個學術共同體隊伍的繁榮壯大,也意味著學術生態環境在優化改善。關于田野調查,上外人已經自覺逐漸形成了共識和風氣,相信未來大家會通過田野工作做出更多有價值的科研貢獻。”
采訪最后,我們談到田野調查的學術倫理。汪段泳認為,研究的終極目標還是“活在當下”。所以,田野調查絕不是把他處看作是“人間動物園”或“歷史試驗場”,而是要時刻懷抱同理心與自省精神,視“他”為“我”,以比較研究的視角,通過代入式觀察,發現我們的過去、檢視我們的現在、估測我們的未來。
他引用當代著名人類學家保羅·拉比諾的話來總結——“通過對他者的觀察,來完成對自身的審視”。